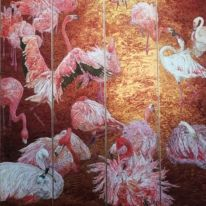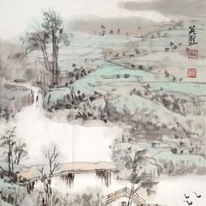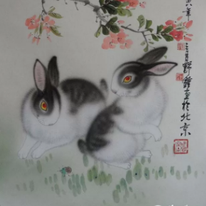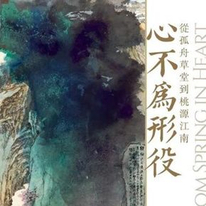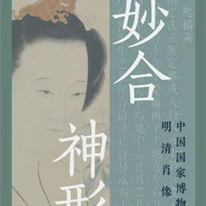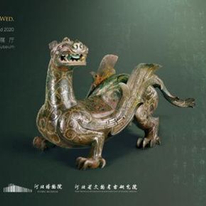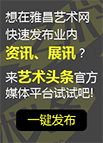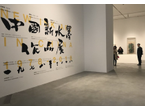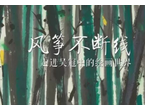新闻正文
赞
相关文章
- 2025-08-21 10:13:45雅昌艺术网起诉ArtPro不正当竞争一案胜诉公告
- 2024-07-09 00:00:00雅昌艺术网 | 重要声明!
- 2023-07-25 09:04:39北京王式廓艺术基金会与深圳雅昌艺术网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 2023-07-24 00:00:00浔陌山水画艺术展即将亮相福建泉州
- 2023-06-22 16:49:55《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30年研究报告》发布
- 2023-03-16 17:33:13全年拍卖快讯发布 雅昌全媒体平台高效解决方案
作品推荐
展览推荐
拍卖预展
- 2022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 安徽省艺观拍卖有限公司
- 预展时间:2030年12月31日
- 预展地点:安徽省芜湖市萧瀚美
- 北京盈昌当代书画专场(十
- 北京盈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 预展时间:2022年3月21日-30日
- 预展地点:北京盈昌网拍
- 北京盈昌当代书画专场拍卖
- 北京盈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 预展时间:2022年3月21日-27日
- 预展地点:北京盈昌网拍
官网推荐
拍卖指数
每日最新
- [新闻] 画家笔下的洋中古镇 | 王来文
- [拍卖] 雅昌专栏 | 朱浩云:超级吃货 深谙美食 ——浅析张大千菜单的市场魅力
- [画廊] 左正尧洛杉矶个展“ 隐匿的回声”正在展出
- [展览] 第十届UABB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OCAT 分展场“平行宇宙”当代数字艺术展开幕 呈现跨文明的对话语境
- [观点] 【雅昌专栏】张辉:文震亨《长物志》的“雅俗”论与明式家具
每周热点
- 1 艺术品消费“吃快餐”,远离了傲慢还
- 2 守护诚信 致力传承,雅昌鉴证备案以领
- 3 央视3·15曝光疯狂的翡翠直播间:古玩
- 4 张大千剧迹《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睽
- 5 “写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对话--孙家
- 6 佳士得纽约亚洲艺术周 | 重要大理国铜
- 7 Poly-Online丨“春意”上线——中国
- 8 XR技术与艺术创作融合的元宇宙虚拟
- 9 专稿 | 是什么成就了加埃塔诺·佩谢
- 10 艺术号·专栏 | 陈履生:画中的少数
排行榜
论坛/博客热点
- 展台上的瓷塑 千军万马战犹酣
- 以藏养藏做再好 终究不如实力雄厚的真玩家?
- 古人烧瓷有讲究 入窑前以煤油遮面以防被偷窥
- 吴伟平:艺术创作,开启了一场没有陪伴的旅
- 杜洪毅:艺术圈里的文字游戏 当代艺术看不懂
推荐视频
业务合作: 010-80451148 bjb@artron.net 责任编辑: 程立雪010-80451148